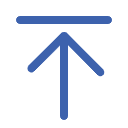肺癌作为全球主要致死性的癌症之一,是医学上需要重点攻克的肿瘤。在评价体内肿瘤负荷方面,宏观视角上的解剖与分子功能融合影像不断进步,微观视角上基因检测及分析技术也是突飞猛进。这两个维度上的巨大进步,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认知,继而治疗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革新。在这个基础上,肺癌的诊疗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今,手术、放疗、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并称为肿瘤治疗的“五驾马车”。其中,放疗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作为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放疗为60%-70%的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即使在肺癌全身治疗手段快速发展的精准医学时代,放疗在早、中、晚期肺癌综合治疗中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贯穿全程。
纵观肿瘤诊疗格局,MDT的思维和实践已经成为肿瘤诊疗中提升疗效和同质化最便捷、最有效和最可及的工具。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中心医院张小涛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肿瘤精准放疗与MDT领域的深度融合。“将职业当信仰,奉疗效为追求”和“不忘初心,医海求索”,正是对张小涛教授匠心追求和高超医术的最好诠释。【ONCO前沿】特邀张教授,带我们畅游肺癌精准放疗领域,传授驾驭肿瘤疗法的金玉良言。
以下视频来源于
ONCO前沿
,时长25:00
专家简介
张小涛 教授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中心医院,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兼立体定向放疗科主任,兼日间诊疗中心主任,青岛市癌症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放射肿瘤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21届“青岛市拔尖人才”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委员会肿瘤代谢学组委员
CSCO血管靶向治疗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学与免疫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小细胞肺癌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放射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肿瘤分会委员/肿瘤姑息治疗委员会委员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JCO)肺癌中文专刊编委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CRTOG执委,肺癌和脑转移瘤委员会常委
青岛市抗癌学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
问题一
在当今时代,要想到达一个肿瘤控制的最佳疗效,您如何理解肿瘤诊疗的整体战略与战术问题?
张小涛教授:
当今时代,达到肿瘤治疗的最佳疗效是患者及家属和医者的共同追求目标。而正确把握肿瘤诊疗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成为所有医生、卫生行政管理者乃至医疗机构应关注的首要问题。这既是一个高大上的哲学问题,也是非常接地气的现实问题。首先,我们通过对各种疑难杂症患者的分析总结后发现,想要取得卓越的疗效,还有赖于明智的整体治疗战略,匹配睿智的战术,便可“执掌乾坤”。反之,我们在对抗肿瘤上,即使战术上再勤奋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错误。例如,进展期胃癌患者过早接受较大手术治疗,导致许多患者无法耐受术后化疗和放疗,这部分过早手术的患者生存期明显不如术前新辅助化疗进行布局的患者。再比如一个优化战术的例子,如果直接给予患者手术治疗,不论使用腔镜手术还是达芬奇手术,都是只是战术上的优化。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充分的分期检查,提前进行准确的分期和MDT和判断患者是否需要术前新辅助治疗,就会在战略上的犯错,此时使用再好的先进手术设备,也弥补不了这种整体战略上的错误,所以不可能得到好疗效。
其次,肿瘤分期是基于既往的成熟经验,参考5年甚至10年生存率将肿瘤患者进行患者预后分层。肿瘤专家应该辩证地看待肿瘤分期指导诊疗的科学意义和局限性。将肿瘤患者分层,目的是指导医生依据不同分期为患者匹配相应的治疗策略,但医生不能完全被肿瘤分期的框架所局限。因此,个人认为肿瘤临床分期的目的是将“瘤负荷”的严重程度进行分层。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实际上又主导我们临床实践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瘤负荷”。只要是恶性肿瘤,就永远存在局部进展和远处转移的哲学矛盾,而“瘤负荷”应该成为肿瘤诊疗策略的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临床实践中有很多病例过程证实,肿瘤患者瘤负荷并不是想当然的,从轻瘤负荷到重瘤负荷的单向性地进展,经过合理有效治疗干预,也存在从重瘤负荷回归到轻瘤负荷状态。例如,寡转移患者的疗效相对较好,说明它的瘤负荷相对较轻,容易得到治疗的控制。因此,“瘤负荷”应成为指导肿瘤全身治疗和局部治疗之间相互转换的“陀螺”。我们曾经收治的一位Ⅳ期肺癌术后的患者,由于术前没有进行充分评估,在某医院的外科仅凭胸部CT诊断为肺癌,直接切除了肺部原发灶,而忽略了术前就存在多发骨转移。最终,这个患者从确诊到去世不足半年时间。这说明我们对“瘤负荷”判断所采取的诊疗策略不准确和不匹配,才最终造成了错误的肿瘤诊疗策略。这也再次印证了我常说的那句话:战术上再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失误,其转归自然的比较悲催。
因此,准确评价“瘤负荷”必须成为肿瘤诊疗决策者的工作重心。纵观医学的进步,我们应该站在更高视角,从以下两个维度评估“瘤负荷”。
第一个维度,从宏观世界角度。即各种医学影像学检查,如PET-CT、磁共振、CT检查和造影检查等,从肉眼能够看见的角度进行评估的手段,我们称为宏观视野角度的“瘤负荷”评估。
第二个维度,从微观世界角度。基因检测分析与解读中的驱动基因、MRD(微小残留病灶)、ctDNA或cfDNA和TMB(肿瘤突变负荷)等,血液循环中肉眼无法看到的微观世界角度评估“瘤负荷”。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提升和经验的积累,微观世界的“瘤负荷”评估已经成为改进肿瘤诊疗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是早期肿瘤患者维持治疗的价值评估。
问题二
您在肿瘤放疗领域颇有建树,并在肺癌、寡转移瘤、脑转移瘤和垂体瘤等肿瘤的临床诊治工作带来了突破性进展。据说你们自己改进SBRT技术,形成独特的OSB放疗技术。借此机会,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团队在肿瘤放射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成就吗?
张小涛教授:
我们团队针对肿瘤放疗领域展开近三十年的探索,专注于寡转移瘤、脑转移瘤、肺癌以及其他良性肿瘤如垂体瘤等诊疗。我们基于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SBRT)和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技术(SRS)进行改造,形成了独特的OSB放疗技术,我们又称之为“洋葱样放疗加量技术”。该技术突破了传统放疗追求靶区内剂量均匀的“调强理念”,形成肿瘤靶区剂量成梯度非均匀性递增的趋势,同时没有突破现有危及器官剂量限制。我们希望将肿瘤的计划靶区(PTV)中的肿瘤区(GTV)病灶放射剂量逐层上调,形成像洋葱一样的形状,直指核心,层层递进,不限制高量,达到能够更好控制肿瘤中耐受放疗的乏氧细胞的目的,不增危及器官损伤的前提下,尽可能达到最大杀瘤效应。这种瘤内非均匀高剂量分布的特点突破了传统“调强理念”的局限性。
此外,在治疗寡转移时,我们会强调整体治疗策略为基础。如驱动基因阳性肺癌合并脑转移患者,在TKI治疗有效的情况下,在颅内iPFS或颅外PFS消失前联合SRS治疗或针对原发灶给予SBRT治疗可以取得更好的疗效,同时减少耐药克隆产生,更好的控制肿瘤。不论是可手术的或不可手术的早期肺癌,还是Ⅲ、Ⅳ期局部或晚期肺癌患者,都有接受精准放疗的机会。但这有赖于我们革新的诊疗理念,以优化的OBS放疗技术(卓越的局部战术手段)融合在科学有效的全身整体治疗策略(精心布局的战略规划),便可以攻克更多肿瘤疑难杂症。
问题三
据我所知,您们精准放疗技术融合在疑难肿瘤的多学科手段取得较好的疗效,尤其是脑转移、SCLC、肉瘤、骨转移等临床实践,请您介绍一下?
张小涛教授: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精准放疗技术一直跟随着计算机和影像技术的迭代步伐,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第一,在疑难肿瘤当中,我们反复尝试将精准放疗融入多学科的临床实践。诸如脑转移瘤的SRS和SRT等技术,如果没有磁共振图像引导技术,放疗技术再好也找不到脑转移肿瘤的治疗“靶心”。因此,这些图像引导等影像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如同放疗技术的眼睛。正是这些不断精进的局部治疗“杀手锏技术”,再与目前日新月异的全身治疗手段(新剂型化疗药物、ADC药物、EGFR/ALK-TKI和抗血管生成药物)融合,为原发肿瘤及其脑转移患者争取到最大生存获益。
第二,小细胞肺癌是最考验一个肿瘤中心综合诊疗水平的疾病。准确地抓住“时间窗口”是治疗小细胞肺癌的关键。“时间窗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局限期到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全身治疗手段和局部治疗手段的切换时间点。只有把握好“时间窗口”,才能有效降伏小细胞肺癌这个“恶魔”。我们团队统计了近几年的50多例小细胞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达23.6%。该数据基于我们自己对小细胞肺癌的全程管理。首先,通过恰到好处的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的切换,在全身治疗有效的情况下,联合改进后的局部治疗放疗技术。其次,局限期和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做好维持治疗也需要高超的艺术。
第三,在肉瘤领域,既往通常应用2 Gy的传统放疗剂量进行治疗,但肉瘤患者,尤其是骨肉瘤和软组织瘤患者的疗效非常差,PFS和OS都非常短。同时,肉瘤极易出现血行转移,为此,我们在全身治疗的化疗和靶向药物的配合下,结合突破性放疗技术,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诊疗方案。如今,我们的单次剂量放疗早已突破了2 Gy,可达到3 Gy-5Gy,甚至更高,疗效也大大提升。此外,我们在前列腺平滑肌肉瘤、胸壁未分化骨肉瘤领域也进行了大量探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肉瘤在不同组织背景下,生物有效剂量(BED)也存在巨大差别,该发现也将对未来放疗的临床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我们在骨转移治疗当中也开展了相关创新实践。随着全身治疗手段有效率的提升,越来越多骨转移患者也取得了长期生存,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既往传统骨转移放疗剂量偏低。既往许多晚期肺癌患者骨转移灶控制不佳,但原发灶控制非常好,这说明传统3 Gy×10次的放疗剂量或者高剂量次数少的放疗方案,并没有有效控制骨转移。究其根本在于对骨转移放疗剂量较低。相对于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突飞猛进,如今落后的骨转移治疗水平形成鲜明的反差,值得我们反思。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问题四
放疗的重要地位我们有目共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临床研究的推进,免疫治疗也进入了大众视野,放疗与免疫的联合也备受关注。您认为放疗和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领域当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张小涛教授:
虽然我的职业始于放疗,但是成于综合治疗。我非常重视放疗及放疗技术更新升级,但是我更重视综合治疗。肿瘤治疗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落伍了。肿瘤治疗绝对需要整合各种有效手段,发挥最大杀瘤效应。目前,放疗在肿瘤治疗领域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人们对放疗仍存在诸多认知层面的问题。不同医院或肿瘤诊疗中心,对于放疗的本质以及放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许多放疗领域的肿瘤医生盲目强调重视放疗,非放疗领域的肿瘤医生仅强调自己掌握的内科治疗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临床研究的推进,放疗和免疫联合治疗方案在越来越多癌种中得以应用,尤其是在Ⅲ期肺癌治疗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如PACIFIC研究中,Ⅲ期肺癌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后应用免疫维持治疗,取得了更好的3年和5年长生存,免疫治疗组的3年、4年和5年OS率分别达到56.7%,49.7%和42.9%。在Ⅳ期肺癌中,寡转移灶应用免疫治疗方案也带来了较好的生存。
但放疗技术如何才能更好地匹配免疫治疗,优化策略组合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直以来,放疗在Ⅰ期至Ⅳ期肺癌局部治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如何巧妙运用放疗手段,使之疗效最大化,在需要放疗发挥作用时如何优化放疗技术,减少放疗带来的损伤,同时又不影响整体治疗策略中后续的免疫或化疗的实施,才是当下最应关注的重点。只有实现局部与整体治疗手段的完美匹配,才能取得最优的治疗效果。
问题五
近十年来,TKI、抗血管药物不断涌现,尤其是肿瘤免疫新药不断上市,放疗是否感受到压力,请问既作为放疗专家又是肿瘤综合诊疗专家,您是如何思考的?
张小涛教授:
近十余年来,TKI、抗血管和免疫治疗新药不断上市,放疗领域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这个压力不是放疗技术本身受到了压力,而作为放疗专家必须不断学习,力争成为更好的肿瘤综合诊疗专家。我们必须掌握全身治疗手段进步的原理,甚至了解外科专家如何进行手术操作,从而改进放疗技术。如果不精进放疗技术,我们将无法抵御TKI、抗血管、免疫治疗,甚至介入治疗等技术带给肿瘤综合治疗的冲击。
如今,PD-L1表达 ≥ 50%的Ⅳ期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了30%。然而,Ⅲc期肺癌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的5年生存率不足30%,这充分体现出Ⅲ期肺癌治疗水平还比不上Ⅳ期肺癌的治疗进步。因此,应当反思如何改进Ⅲ期肺癌的治疗策略?在免疫时代,放疗如何与PD-L1和CTLA-4单抗有机融合?如果放疗提前应用是否会阻碍后续免疫药物的应用?究竟如何布局才能为Ⅲ期肺癌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这一切都仍需思考。因此,我认为如今的放疗技术仍需改进,应批判性思考既往传统放疗对放射靶区的设定,并进一步缩小照射范围,减少照射野中的淋巴组织或者血管,从而降低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如果放疗靶区范围没有缩小,放疗剂量就很难提高。因此,我们改进放疗技术的核心,就是缩小照射范围,将放射线精准的聚焦在需要照射的肿瘤GTV上,同时又照顾到亚临床病灶,这样才能更好的将精准放疗技术与不断进步的全身治疗手段相匹配。
比如EGFR阳性的Ⅳ期肺癌,不论是脑转移还是骨转移患者,有效的TKI治疗可缩小转移灶大小。但如果想要继续提高对转移灶的控制率,必须在TKI的PFS消失之前将放疗引入,才能延长患者生存。此外,应用抗血管联合TKI药物的A+T方案,不论是对比一代还是三代TKI,它们对OS的延长仍较为有限。其根本的原因还要归结于晚期肿瘤患者,不单单要控制局部肿瘤本身,还要预防肿瘤的并发症,如血栓、营养不良、感染和出血等。只有在有前瞻性的肿瘤整体治疗策略引领下,做到综合治疗手段有计划的融合,才能带来更好的疗效。
寄语
总之,时代在进步,肿瘤专家必须结合宏观上的影像学检查和微观上的基因检测两个维度,综合的准确地评估“瘤负荷”,才能为指导肿瘤诊疗制定最佳的战略与战术。同时,全面了解和掌握肿瘤治疗的“战术”,如外科手术、基因检测、药物进展、免疫治疗、优化放疗技术等,才能将“十八般兵器”玩得得心应手和炉火纯青。
肿瘤诊疗方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在做好医患之间有效沟通和积极沟通基础上,争取做到战略上正确,战术上优化,“瘤负荷”为引领,把握好局部和全身治疗手段的切换的时间窗口,最终实现肿瘤诊疗的远大理想目标。
Copyright©2021
深圳裕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61288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