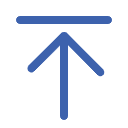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官网数据显示,胃癌是中国第三大常见的新发癌症。大多数患者确诊时为临床晚期,化疗为晚期胃癌患者主要的治疗方式。近年来,胃癌领域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研究硕果不断,打破了目前晚期胃癌以化疗为主的现状,免疫治疗也逐渐从晚期胃癌的后线治疗迈入一线治疗,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作为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关键点,其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也成为了胃癌免疫治疗研究的热点。ONCO前沿小编对刘联教授就免疫治疗biomarker相关问题进行采访。
专家简介

刘联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免疫学博士后、肿瘤学博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山东免疫学会肿瘤分子标志物与靶向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营养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CGCA)内科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山东免疫学会理事
山东省医学会姑息医学分会青委会副主委
山东抗癌协会化疗分会委员兼青委会常委
山东疼痛医学会肿瘤整合医学专委会副主委
山东医师协会肿瘤精准医疗分会、肿瘤MDT专委会常委
国家食药监局新药审评中心数据核查员
教育部学位中心全国博硕士毕业论文评议专家
山东省科技专家库基金评审专家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库成员
《Cancer cell research》、《精准医学》、《国际肿瘤学》等杂志编委
问题一
美国FDA加速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含氟嘧啶类/铂类)用于HER2阳性不可切除局部晚期/转移性胃癌的一线治疗,这种用药方案在胃癌围手术期能否占有一席之地?
刘联教授:
晚期胃癌已经迎来了免疫治疗或免疫联合治疗时代,免疫治疗也已占据一席之地。CheckMate649研究的成功,以及最近加速获批的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一线治疗HER2阳性的晚期胃癌患者,都告诉我们免疫治疗虽然在胃癌领域的探索还有很多波折与挑战,但离成功会越来越近。因为对于胃癌这样一个冷肿瘤或异质性比较强的肿瘤来说,患者很难从单纯的化疗或靶向治疗中获得较为显著的生存期延长,但是免疫治疗或许能够对这些高异质性、高TMB的肿瘤有相对不错的疗效。对于晚期胃癌来讲,免疫治疗在未来会是疗效获得突破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手段。
对于围手术期胃癌的治疗,也就是针对早期或局部晚期的胃癌来说,目前可能缺乏一些大型III期RCT研究的数据,但这并不影响世界范围内医生和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展开广泛的探讨。其中针对可手术患者的术前治疗,采取PD-1或PD-L1联合标准化疗方案,如SOX或FLOT4方案,一些小型II期研究报道的pCR率约为10%,总体来说疗效虽然不如非小细胞肺癌,但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对于术后治疗,其实是贯穿整个围手术期治疗的一部分,可以免疫治疗为基础,再联合其他治疗,如化疗等。DANTE研究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FLOT方案用于潜在可切除性局部进展期胃或胃食管交界腺癌的围手术期治疗,目前疗效还未报告,但安全性较可靠。国内外学者所做的其他II期研究也表明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在术前术后总体上安全可靠,并且疗效相对来说也不错,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未来如果能够通过III期研究,验证得到较好的pCR率、降期率、R0切除率,甚至还能为患者带来更长的DFS、OS的话,就可以进一步证明采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进行围手术期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另外,在围手术期胃癌的治疗中,还有一些比较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将晚期胃癌中所应用的一些治疗模式,移植到早期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中。在晚期胃癌的治疗中,不仅仅有免疫联合化疗,还有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免疫联合免疫治疗,同时针对HER2扩增的胃癌患者,还有免疫联合曲妥珠单抗的治疗,很多药物的联合治疗都带来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如果把这些模式移植到早期胃癌的围术期治疗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前途的探索方向。我们也有相关研究正在开展,包括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然后再结合化疗、放疗、抗血管治疗、靶向治疗等,其中在药物的选择上既有大分子抗体也有小分子TKI。总之,我们的治疗手段是很丰富的,通过多管齐下,有可能使胃癌治疗在手术前就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从而给外科专家们创造一个较好的完整切除或根治性切除的条件,如果这样能达到R0切除的话,可想而知患者一定会获得较显著的生存延长。当然这些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最终的结果还需要大型三期RCT研究来证实,但我对这些研究的结果充满了信心。
问题二
胃癌常见的免疫标志物,如PD-L1、MSI、TMB、EBV等,那么哪些生物标志物在胃癌免疫治疗治疗领域更具优势?这些生物标志物甚至靶点之间又有着哪些千丝万缕的关联呢?
刘联教授:
对于胃癌来说,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biomarker主要还是集中在晚期胃癌相关研究的证据上,也就是说没有太多新的发现,和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biomarker是接近的。比如在胃癌领域我们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公认的biomarker,如PD-L1的表达、TMB以及MSI-H这三个指标,我想从广义上来讲,它们适合所有肿瘤,对胃癌也不例外。
其中PD-L1的表达,虽然在胃癌的研究中也有争论,但是它是目前最成熟的,大家最广泛接受的biomarker,同时,不管是在一线治疗还是二线治疗,甚至是在早期的一些转化治疗中,PD-L1的表达和免疫相关治疗疗效都是密切相关的。而对于TMB,这一指标在很多肿瘤中也存在着争议,在胃癌领域也有相关的探索,如KEYNOTE-061研究,虽然研究结果可能是阴性,但是2020ASCO也报道了对于TMB高的患者,患者能够从免疫治疗中获得显著的生存获益。因此,TMB对于胃癌免疫治疗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预测价值,但TMB指标的落地性和实用性还有待加强。此外,MSI-H在临床中的应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争议较少,在肺癌、晚期结直肠癌、黑色素瘤和胃癌等领域都有很好的预测效果,不过MSI-H的整体检出率都不高,在胃癌中的表达率也偏低。除上述三个指标外,由于免疫治疗在EBV相关的患者中疗效较好,所以EBV也被看做为胃癌免疫治疗中一个独特的biomarker。
那么这些指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PD-L1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指标,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通过肿瘤组织检测来获得,包括TPS、CPS评分,但是PD-L1的表达也分为固有性表达和适应性表达,即虽然PD-L1的表达和其他biomarker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可能是互斥关系,但是它本身的表达也是动态变化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只检测一次PD-L1,就决定患者终生能不能应用免疫治疗可能是不充分的。CheckMate649研究是目前唯一取得阳性结果的III期研究,该研究表明PD-L1 CPS≥ 5的患者获得了OS和PFS的显著获益,所以说PD-L1的表达和检测的准确性,以及其动态监测是非常重要的。而TMB和MSI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微卫星不稳定,就可能会导致DNA的断裂、错配及修复障碍,如果修复不及时就会产生大量突变的基因,这些突变的基因就可能会导致TMB增加,TMB增加就会导致新生抗原增加,从而激活更多的淋巴细胞,可见如果是MSI-H的患者,TMB一定会增加,但是TMB高的患者未必是MSI-H,因为DNA修复有八大信号通路,而MSI-H只是其中的一条,这告诉我们探索更多的DNA错配修复通路的相关基因,可能给胃癌,乃至所有实体肿瘤带来一些更好的biomarker,比如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POLE、POLD以及CHEK1、ATM等指标,如果有突变,可能暂时没有合适的靶向治疗药物,但是这类患者可能是免疫治疗的优势人群,所以这些指标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探索。当然EBV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我们知道2014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TCGA胃癌分型,EB病毒感染型(EBV)患者的肿瘤标本中PD-L1和PD-L2的表达是增高的,这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EBV病毒感染的胃癌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特别好。韩国学者的研究表明,EBV、MSI-H、PD-L1、TMB等指标,如果有一项高表达或者是阳性,患者采取免疫治疗的疗效就会不错,但是这些指标的比例、有效率并不完全一样;而如果这4项指标都是阴性,胃癌患者可能就很难从单纯的免疫治疗中获益;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联合检测可能会更具有预测价值;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指标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采取联合治疗,需要把冷肿瘤转换为热肿瘤,这些工作也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问题三
众所周知,胃癌是免疫治疗的“冷肿瘤”,相对其他肿瘤而言,胃癌免疫治疗进展相对缓慢,那么对于如何将“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当前是否有新的研究进展?
刘联教授:
胃癌的免疫治疗进展确实相对缓慢和曲折,但是可能我们也别无选择。因为对于胃癌来说,化疗已经达到了瓶颈,靶向治疗的探索也面临较多失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胃癌的异质性非常强,缺少一个一统江湖的靶点,所以无法在靶向治疗中有充分的获益。目前可能只有HER2扩增的胃癌患者能够从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中获益,但这部分病人在国内可能不到10%。也就是说免疫治疗时代,可能也只能依赖免疫治疗给胃癌患者带来更大的生存获益的突破。
胃癌作为冷肿瘤,其免疫微环境中CD8+T细胞较少,而抑制性的细胞较多,或者肿瘤细胞表达的抗原较少,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或处理来改变,即改变肿瘤的免疫微环境,可采取传统的治疗模式如化疗、放疗、甚至是结合部分靶向治疗,虽然这些治疗难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但可以发挥杀死局部肿瘤细胞的作用。肿瘤细胞一旦被杀死或凋亡后,就会释放相应的抗原,从而抗原递呈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将抗原递呈给相应的T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被激活后就能够识别和杀死肿瘤细胞,而这个过程如果遇到了抑制性的信号通路,此时我们采取相应的药物去逆转这种抑制,这也是免疫治疗的基本机制。所以,我们首先可通过传统的方法让肿瘤细胞释放抗原,让它递呈更多、更全面的抗原从而吸引淋巴细胞浸润和杀伤,这也就实现了从冷肿瘤向热肿瘤转化的过程。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包括在其他肿瘤领域常做的抗血管治疗、免疫活化因子的加入以及针对免疫微环境中非T淋巴细胞的一些免疫细胞的干预,比如几类常见的免疫抑制细胞TAM(肿瘤相关性巨噬细胞)、CAF(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Treg(免疫抑制性细胞)、MDSC(骨髓来源的抑制细胞)等,若采取一定手段进行干预,这些细胞的抑制作用可能会被逆转或者被消除,这样一来,CD8+T细胞就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能够识别和杀死肿瘤细胞。当然这些探索非常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PD-L1、PD-1和CTLA-4以外,还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如TIM-3、LAG-3、Siglec15等,以及在肺癌领域已获得部分成功的TIGIT等,这些靶点都是免疫检查点家族有待挖掘的金矿,而且国内外药企的研发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对于未来,无论是针对免疫检查点靶点的丰富、研发和突破,还是对免疫微环境中的各种免疫细胞包括免疫激活细胞、免疫抑制细胞进行干预,以及对免疫环境中相关细胞因子进行干预,最终都可能使我们对冷肿瘤向热肿瘤转化的探索获得突破。这主要依赖于基础研究中首先获得突破,然后进行转化研究的探索,然后进一步开展大型III期研究的验证。相信随着这些系列研究的进展,会逐渐丰富目前临床的治疗手段,从而在未来使胃癌患者获得更好的疗效、更长的生存获益。
Copyright©2021
深圳裕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6128839号